
昨天寫文章容易,隨便一句什麼話,後面接「這像極了愛情」就好。為了不離題,我打算直接寫愛情。
這幾天我在看宇文所安的《只是一首歌》,英文名是《Just A Song》,用失而復得的偷窺欲去看的。書講的宋朝,那種盤旋在商業買賣與稀有愛情之間的斡旋。
柳永是那時「類青樓」女人們,以及達官顯貴們的精神幻象,時至今日也是不少用「肉體自由」來標榜「精神風雅」的男人們的談資。他,既是浪子,又能為愛不回頭,女人在他筆下不再是精英文化裡一個又一個的情感容器,但他又忍不住消費她們,同時提供可貴的精神溢出物。我相信,邏輯上不狗血的電視劇通常紅不了。
那時候的「妓」理解為妓女其實並不準確,我說的「類青樓」指的是,她們主要負責在筵席或其他飲酒場合陪伴官員,提供音樂助興。因為卑微,表演又難免出現郎情妾意的情境,所以常被席上官員當臨時伴侶。最高級的私妓不同,那是明星一般的存在,所以可以與男性討價還價,她們也對這種「反向物化」充滿優越感。男人本身的回饋,不必是金錢,最好是「真情」。 11世紀《玉蝴蝶》中,一位舊相識把柳永帶到臥房,“親持犀管,旋疊香纈,要索新詞,氫人含笑立尊前。”擁有一首“新詞”能夠提升一個私妓的資本。這個過程就很像比爾蓋茲說的伴侶之間要「raise each other up」(互相提升)。
「妓」其實是依照「伎」來分級的。歌妓要辛苦一些,私妓那拿到本子,把詞作記誦下來,才能表演,這種通常是小令。從宋詞內部文本證據可以知道,宋宴持續時間相當長,所以一名歌妓得有足夠的中華曲庫資源才能撐足一個長時間的歡宴。一旦主人把家財散盡,歌妓酒使也會各散東西,帶著表演投奔新主人,於是「新詞」唱成了舊詞。好的官妓就能去唱“慢詞”,也就是表演長歌詞,還得唱得深情款款,就更有難度。正如柳永想像愛人如何寫下了他眼下正在閱讀的信。這樣的萍水相逢,可能是無數次的新詞重演,儘管每一次都有欣喜,摻雜著倦怠,很少有雋永的,無論如何“飽含真情的忠貞”成為一種情緒價值,可以“raise up”的那種。
表演的情境感很重要,柳永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個戲劇大師。因為情郎不在身邊,詩裡的傳統女子總是「懶」得梳妝打扮,也總為伊消瘦。柳永在詞裡陳列女子的不渝,也展現男子的長情,樂此不疲。他在《慢捲軸》中以一貫的姿勢輾轉難眠,思念不在身邊的戀人,想像她因為思念而神傷“又爭似從前,淡淡相看,免恁牽系。”理解愛情發生在“初見”,才能讀懂“淡淡”,兩人或因分隔兩地漸漸疏遠,可是那莫名的牽引還在。當這種情愫被善於成為男人慾望對象的表演者傳達出來,就成為一種跨越時間的「團購」。她銷售的不是性,不是愛,而是幻象,供權貴們競購瓜分,甚至價高者還能私人訂製。表演要到藝術家的級別,需要以情動人,就像柳永說的「須信道,緣情寄意,別有知音」。不管詞是不是在「真心話」和「看似真心話」邊緣玩火,情到深處,蠟炬成灰,那知音難免來一兩個。柳永最著名的一首叫《定風波》,繼續是“閨怨”主題,“自春來、慘綠愁紅”,“恨薄情一去,音書無個”,最後勸人“免使年少,光陰虛過」。從側面看,多情還是愁債的。根據羅大經《鶴林玉露》所載,柳永到杭州後,得知老朋友孫何正任兩浙轉運使,就去拜會孫何。無奈孫何的門禁太嚴,柳永是一介布衣,無法見到。
浪子柳永一直不得志,到處飄泊,流浪花巷,消解煩愁,其實也是順便尋找晉升的途徑。見孫何的事,促使柳永寫了《望海潮》“異日圖將好景,歸去鳳池誇”,意思是“他日把杭州美景畫出來,回朝廷升官時向人們誇耀。”柳永請了當地一位著名的歌女,吩咐她說,如果孫何在宴會上請她唱歌,不要唱別的,就唱這首《望海潮·東南形勝》。這首詞是一首幹謁詞,目的是請求對方為自己舉薦。結果孫何沒動靜,某日金國皇帝一聽到這首歌,倒對杭州心生嚮往,動了南侵的念頭。
末尾,放點感動我的老美食照片,保證比渣男聲名遠播的謊話感動。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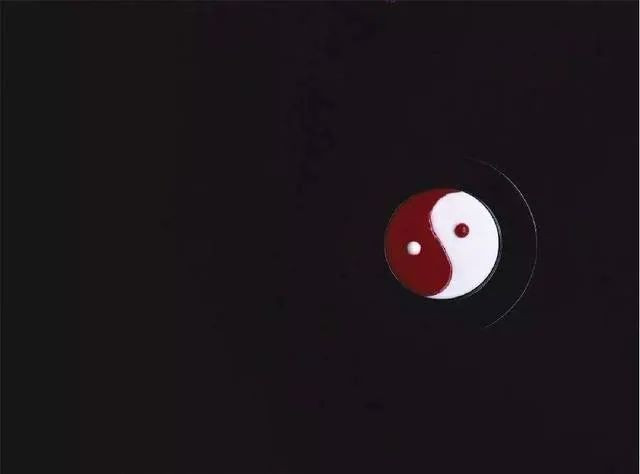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德國攝影師Wolf Reinhart在上世紀80年代拍攝,他1985年出版的《China\'s Food - A Photographic Journey by Reinhart Wolf》記錄了他在中國看到的美食。


